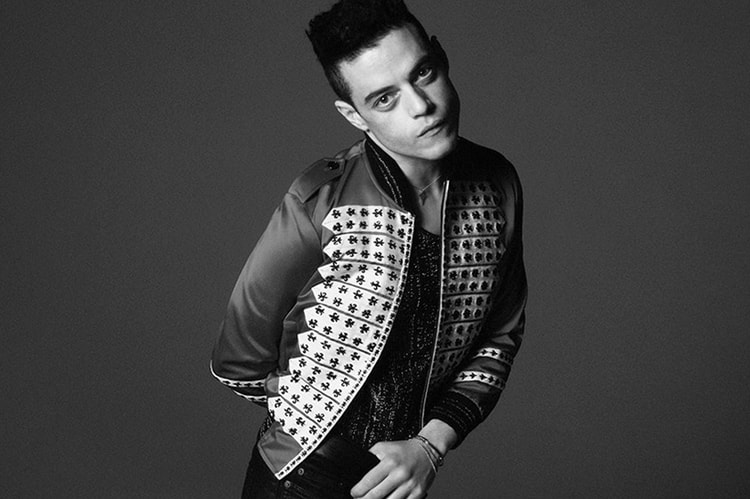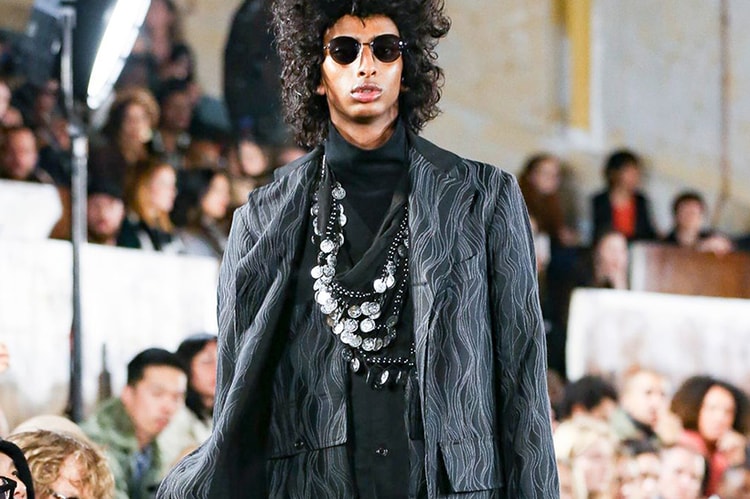《Sneaker Freaker》主腦 Woody Wood 親述成立雜誌的故事與歷年見聞 | Business of HYPE
Woody:「這個時代大家喜歡追逐潮流,跟明星穿一樣的鞋,但我們在舊時候卻是開創潮流!」

在本期 Business of HYPE 中,我們邀請到了來自《Sneaker Freaker》的創始人 Woody Wood 在訪談。在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上學時,Woody 就開始利用 QuarkXpress 作為校報的編輯,當是他僅花了一星期的時間便以一台 Nikon Coolpix 相機與一部電腦完成了第一期。《Sneaker Freaker》更獲得了 Nike 的青睞,更一舉進入全球市場。在對談當中,Woody 更與我們分享了《Sneaker Freaker》的創立理念、對紙媒的看法以及與各品牌合作的趣事。

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嗎?
我不希望別人稱呼我為主編,除了是太過官方之外,我更認為這並沒有準確的描述當中真正的工作。我更像一間公司的總裁,所有的事情也需要處理,畢竟當時《Sneaker Freaker》公司不大,我一個人要幹的事情可能相當於 15 份工作。
可向我們介紹一下《Sneaker Freaker》嗎?
我覺得要分為三部分,首先《Sneaker Freaker》是一家文化公司,通過各位知名的球鞋收藏家來講述關於這個行業的知識來創作內容,包括行業故事、品牌歷史、員工軼事等等,有可能我們比起 Nike 的員工還要了解 Nike,我們同時還會在網站和社交媒體上發佈內容,最後就會大家所認真的雜誌。
雜誌開始時,只用一台 Nikon Coolpix 相機與一部電腦完成了第一期。
你怎麼看待很多人說「紙媒已死」這個觀點?
我真不這麼認為紙媒已死,因為紙媒最大的優勢是它遠比 Instagram 等等社交媒體平台便宜,只要找到目標讀者群,印幾本書根本花不了幾多的資金,就如音樂與實體唱片的關係,總有人喜歡 CD 的質感,然而困難的地方是如何找對目標用戶,並讓他們看到雜誌的存在。我們曾經也做過數字雜誌,就是那種用鼠標翻頁的。初期免費的時候有超過 50,000 的訂閱,但是當我們開始收費就沒剩下幾個,那麼最後我們還是回到以紙媒為主導的模式。


那麼《Sneaker Freaker》以品牌合作的內容為主還是只是單純的東西?
大多都是與品牌合作的內容,類似特定某款鞋的文化與歷史。之前完成了 New Balance 的 574 和 997 兩款鞋的專題。如果要寫 Air Max 的歷史,我閉著眼睛都能寫 5,000頁 出來,但是 574 是一件很樸素的鞋款。New Balance 發展至今,如要說它是最暢銷的鞋款也不為過,但就是因為它太過樸素,所以沒多少人願意去了解或是收藏它,最終我們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收集和處理資料,但是能夠了解並發掘這些背後的故事讓我感動相當的興奮!
介紹一下《Sneaker Freaker》之前與 Taschen 合作出版的《The Ultimate Sneaker Book》嗎?
這本書原本是《Sneaker Freaker》計劃的十週年特刊,但碰上 2012 年的金融危機,雖然對於澳洲沒有太大影響,但是世界範圍的紙媒都在衰落,所以我們就一直忽略了這個項目,慢慢地寫了五年後,便成為了十五週年的特別企劃。我幾乎把自己對球鞋所有的知識都寫進了書中,成書最後 650 頁,但實際上還有另外 400 頁已經寫好了九成,相應第二本也許在不久的未來就會發布。這本書沒有任何品牌的商業推廣,是一本真真正正的球鞋愛好者天書。

《Sneaker Freaker》一共有多少員工?
我們員工不多,只有 18 人。我們一直希望能找到更多既有淵博球鞋知識,又有專業的技能的人,你可以在世界上任意一個地方工作,辦公室裡我們只有 14 個員工。本身我們編輯部在墨爾本就讓少數人都不敢相信,我不止一次被問到我們編輯部是不是在紐約或倫敦。
《Sneaker Freaker》怎麼將影響力擴展到全球?
《Sneaker Freaker》一直在多個市場與不同品牌合作,雖然紐約和美國的面積差不多,但我們的人口只相當於紐約市人口,如果僅靠本地的讀者,我們的預算會相當小,也沒法像現在這樣做 547 和 997 的專題。我們希望將《Sneaker Freaker》定位成一本專業的球鞋雜誌,如想探索任何一件冷門或熱門的球鞋,希望第一時間也會想到《Sneaker Freaker》。在整個市場上基本沒有第二家媒體可以達到這個領域,所以更需要精益求精,認真對待內容處理。其實我幾乎 24 小時都在工作,聯繫世界各地的人。
還記得《Sneaker Freaker》第一期雜誌的封面是哪雙鞋嗎?
當然記得,是一雙 Nike Air Force 1「Year of the Horse」,這雙鞋太容易壞了,無論穿不穿它都會自行解體。第一期雜誌有 32 頁,當時的製作目標並不是要成為一本專業雜誌,只是一本自製讀物,所以我一直沒有給雜誌加上頁數,甚至都沒有目錄。

甚麼時候開始有盈利呢?
其實一直也有盈利,因為我們的定位特殊,一本來自澳洲的球鞋文化雜誌,媒體都認為很新奇,所以也有很多報導,很快就開始要學習如何做國際發行,畢竟不可能一直從第一期雜誌開始,我就開辦了《Sneaker Freaker》的網站,你現在還能在 Wayback Machine(網頁檔案館)看到我們剛開始的模樣。當時只有一台 Nikon Coolpix 相機,120 萬像素,幾乎沒有任何景深,直到 Canon 5D 上市,才逐漸學會專業的攝影技巧。
《Sneaker Freaker》的第一個合作品牌是甚麼?
Nike!他們很擅長發掘新事物,他們給了我們向世界展現自己的機會。

在創立《Sneaker Freaker》之前,你一定也是個鞋迷,對嗎?
我的確是一個典型的球鞋迷,年輕的時候到大城市第一件事就是去球鞋店購買球鞋,不過澳洲的球鞋都偏貴。1998 年當時有一對 Reebok INSTA PUMP FURY 1st 很想擁有,價格是 340 澳元,相當於今天的800 美元,喜歡球鞋的契機其實不太明確,就是六年級的某個下午,我突然對自己所穿的球鞋著了迷,想要去了解它,那時候我穿的是一雙 Dunlop KT26,你們可能都不知道這個牌子,它的外型就像一雙 New Balance 574。

在這 15 年來,球鞋已經發展成為了一種成熟的文化,甚至是時代的潮流,甚至部分人只是將球鞋作為生意,還是有很多人被球鞋改變了自己的生活,你如何看待這種趨勢呢?
《Sneaker Freaker》作為鞋迷和品牌之間的中間人,在新時代下,從事社交網絡的發展,鞋迷甚麼與品牌之間的關係拉近了,品牌一定會對球鞋迷的意見有所反應,而我更希望《Sneaker Freaker》成為一個雙方對話的平台。
你認為球鞋這個市場會一直繁榮下去嗎?
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創新意識,過去幾年 Nike 與 adidas 一直此起彼伏,adidas 的 Ultraboost 與 YEEZY 熱潮不斷,但隨之就止步不前,反觀現在又回到了 Nike 的時代。這其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,整個行業一直都是這樣發展,變速的繁榮後肯定會有沉澱的沉澱。

每年也有那麼多的新鞋推出,你認為市場接近飽和了嗎?
我自己有 600 多雙鞋,但我每個月仍然會買兩雙新的。只要市場上有創新,那麼飽和就是假命題。很多小公司想在這行業分一杯羹,那麼它們就要刺激大公司不斷創新,或者重啟以前的鞋款,類似 adidas 的 Stan Smith,又或是 Nike 的 Air Force 1。每年的聯名鞋作也如此多,我們真正需要擔心的是現在這個時代孩子們都喜歡追逐潮流,跟明星穿一樣的鞋,但我們在舊時候卻是開創潮流,例如我當時非常喜歡 Nike 的 ACG 登山鞋系列,在今天這款鞋子毫無疑問是不會流行的。
這個時代大家喜歡追逐潮流,跟明星穿一樣的鞋,但我們在舊時候卻是開創潮流!